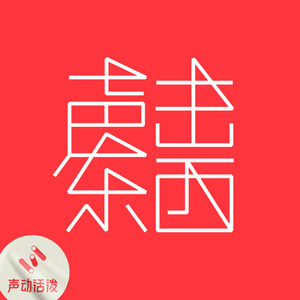昨天和轻芒的创始人王俊煜做「硅谷早知道」的访谈,聊 Apple 的新付费服务News+。
其中提到了The Daily,一个旧媒体为了应对挑战而试图创造的新媒体。但这个媒体刚诞生没多久就夭折了,当时我在「第一财经周刊」还写过它。六七年过去,「第一财经周刊」也不再存在,当我试图去网上找我当年写的这篇文章时,只在某个人的新浪博客中找到了它。
还是蛮感伤的。把它贴在下面,也算是往日工作的一个纪念吧。

最后一期
《新闻周刊》和The Daily是不同的,一个是旧帝国,一个是新世界。但它们都失败了,在残酷的12月。
文|CBN记者 徐涛 杨樱 俞斯译 张晶 实习记者 邱悦 胡吉
制图|项凯
12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收了订户全年订费的报业发行商们,勉力坚持到年底,然后,出版最后一期。
这个冬天,轮到了《新闻周刊》(Newsweek)。这份杂志在它80周年创刊日之前,将停止它的纸质版本,然后开启它完全数字版的Newsweek Global。
谁也不知道这个行业里漫长的死亡还要延续多少年。从1990年代开始,美国报业1/4的工作岗位已慢慢消失。经年累月,记者们要习惯这种可悲又奇怪的双重身份,他们在不断报道自己这个行业可怕的新闻,例如《纽约时报》不得不出售返租自己刚建成的豪华大楼,或论坛报业集团的濒临破产。
“正因为是《新闻周刊》,它才获得如此之大的关注。其实它的失败跟其他籍籍无名的媒体的失败没什么两样。他们出问题了,尝试过了,失败了。就是这样。”哈佛商学院研究媒体的教授Bharat Anand对《第一财经周刊》说。
不仅仅因为是《新闻周刊》,还因为是Tina Brown。
一些人认为Brown能让这家刊物好起来。她曾经拯救过《名利场》。在Brown于1980年代进入这本杂志时,《名利场》有着7000万美元的亏损,正在死亡边缘。Brown主导这本杂志与最有才华的作者与摄影师签约,让它成为明星八卦和严肃话题的混合体。这本曾被她嘲讽为“自命不凡,毫无幽默感,不聪明,很乏味”的杂志很快在她手中从20万发行量上升到了120万。在她离开时,《名利场》已有800万美元的盈利,以及声名赫赫的品牌。
这位纸媒业的传奇人物又在《纽约客》复制了同样的故事,她也多少改变了这本优雅杂志的基因。在Brown的任期,《纽约客》4次获得乔治·波尔卡新闻奖、5次海外新闻协会奖和10次国家杂志奖,发行量也从1992年的66万份增长到了1997年的81万份。
当音频设备富翁Sidney Harman (2010年,他从急于摆脱《新闻周刊》的华盛顿邮报集团那里将这个带有4700万美元债务的杂志以1美元的代价买了过来 ),把希望交到Tina Brown手中时,后者已经创立了自己的数字媒体品牌The Daily Beast,是的,她本人也已经变了,不再只是纸媒业的象征。Harman在争取到这次合并后说,“这将已经建立的新闻的权威和光明的生机勃勃的互联网结合在了一起。”
《新闻周刊》已经在之前的3年间丢失了一半的发行量,从2008年初的310万份到2010年的150万份,但在Brown主导后,《新闻周刊》一度看起来情况不错。最初的两个月,其在报刊亭的销售额比2010年同期上升了57%,一些广告商例如欧米茄手表又重新回来了。
但似乎这种坚持不可能比两年时间更长了。和在《名利场》及《纽约客》做的努力类似,Brown竭力为《新闻周刊》挖掘名人新闻,制造话题。她接管后的第一期是关于希拉里·克林顿的。
但这并不足以挽救一个旧帝国。特别在Sidney Harman突然去世之后,原来的《新闻周刊》的命运就只能是走向死亡。“20年前我居住的小镇上有两份报纸,竞争很简单,A只要和B不同就好了。但现在可能存在一百种不同的竞争,一份杂志,它只是另一份这个,另一份那个,它一定会有麻烦的。”Bharat Anand说。
Brown做出了自己的决定。她说:“大象不能跳舞,新的帝国会建成得很快。”
这里曾经有可能出现一个新的帝国。
在新闻集团位于纽约曼哈顿的大楼内,The Daily的一些人在制作视频和照片,他们将翻唱的“So Long,farewell”的视频放在了Twitter上,这个视频有着一种试图幽默但却难抑悲伤的调调;另一张360°旋转的照片是坚持到最后的90多名员工的合影。在这里,The Daily正式走向了终结。
作为世界上第一份iPad报纸,The Daily在最后一期上的告别看上去更炫一点:封面“谢谢&再见”背景下是动态图片,滑动的时间轴展示了这份报纸所经历的所有新闻大事件;当然还包括那些视频、封面合集,还有填字游戏。
12月15日,The Daily发行了它的第682期,最后一期。
在2011年2月创刊时,The Daily的确算是当时悲观气氛中的乐观产物。即使今日回顾,它看上去也依然有很多理由让人对它的成功抱有希望。
它只在iPad上发行;它有来自新闻集团的充足预算;它组建了一个即使不是最优但也足以堪称豪华的团队。
在The Daily名字尚未确定时,默多克就请来了Ceros的首席科学家和创始人Brian Alvey来建立一整套的底层技术。当时所有的媒体都在费力地将印刷版本变成超过几百兆字节的PDF版本时,这个技术团队做的是让The Daily能将每天出版的120多页视频之外的内容控制在20兆以下。
The Daily还有着履历不凡的采编团队,他们来自ABC新闻、《纽约时报》、《纽约邮报》或者《纽约客》。而设计师团队让The Daily受到了乔布斯的认可。
这些人挤在同一个办公室像创业者那样并肩作战。 “早期的日子很有趣。” Peter Ha说,他是The Daily的第19号员工,参与了最初的创刊,“人很少,挤在新闻集团26楼北侧俯瞰48街,有一种一家人的感觉。”他将一张创刊时同事加班后猫在公司椅子上睡觉的照片发到了网上。
默多克常在The Daily主编和发行人的办公室中晃荡;有一天他甚至带着U2 的主唱Bono来和大家打招呼。
The Daily在2011年度是苹果应用商店中下载量前三的应用程序—排在其之前的是《愤怒的小鸟》和《蓝精灵村庄》这两款游戏;如果按照销售额,那它能排在首位。
但如果今天再细细想一想这件事,全球最大的媒体集团之一,为了一个公司推出的新产品 — — 哪怕这个公司是苹果 — — 而真的设计了一种全新的产品,这本身多少透露出一点慌乱来。而这又加重了窒息气氛,如果说早先大家觉得只要拥抱科技事情就能好起来,现在看起来也不全是这样。
“本来每个报纸都好好的,直到颠覆性的技术革新到来。我想接下来十年互联网和印刷版的新闻会共存。一些人说是五年,我倾向于说是二十年,但这二十年也意味着发行量很小的二十年。”默多克说。
“人们会因为害怕,就觉得自己总得做点什么。但我要说,你不能为了试而试,”Anand说,“最困难的其实是你什么都不去做。”
但媒体等不及都要做点什么。皮尤研究中心9月的数字说,在30岁以下的人群中,只有13%的人依然还在读报,不论是印刷版还是电子版。随之而去的是广告。在几年间,Craigslist这样的网站迅速成为平媒上分类广告最好的替代者;除此之外,惊慌失措的广告商纷纷将更多的钱投到互联网关键词广告、展示广告,或是新鲜但并不知道效果如何的营销应用程序上。
MPA(美国杂志联合协会)的数据显示,美国整个杂志行业的广告在最近4年缩水了1/5,从2007年的255亿美元到2011年的200亿美元。
“我的确对新闻业的未来很担忧,这个行业此前由广告收入所支撑,但现在越来越多广告会流入到社交媒体,再也回不来了。”Reed Phillips在接受《第一财经周刊》采访时说。他是投资银行Desilva&Phillips的CEO,这家公司专注于媒体投资和交易。数年前Harman买下《新闻周刊》的时候,他说Harman不过是把这个看成是一个爱好,而不是投资。
默多克希望The Daily的这次数字实验能够带领他的媒体帝国转型,但这种被赋予的未来显然没有成为现实。在宣布停刊之后,The Daily主编Jesse Angelo和发行人Greg Clayman对读者说:“The Daily的确是个不可思议的创新载体,我们很自豪我们所做的那些突破性工作,但是最终,我们还是没能增长到拥有足够的读者。”
问题是,The Daily的今天会是《新闻周刊》数字版的明天吗?
可惜的是,在两年之前,似乎没有人看到The Daily这个产品背后隐藏的荒诞。
苹果公司的iPad在2010年4月刚刚推出的时候,似乎就成为了传统媒体人的拯救者。根据市场研究公司McPheters&Company的监测,在那一年的第二季度,美国杂志发布了98个iPad应用。到今年第一季度,这个数量已经增长到1159个。
这个时代和创造出默多克以及Brown成功的那个时代相去甚远。那时新闻并不触手可及,人们每天会在早餐桌边打开报纸去了解世界,或在大事发生后冲去报刊亭同时买上一份《时代周刊》和一份《新闻周刊》。
那个时代也是记者作为意见领袖的时代,他们比别人有更多的信息,也因此更加权威。人们为这些信息和意见埋单,广告商乐于将自己的广告放在他们的专栏旁,而媒体则慷慨给予最好的记者以重金—《新闻周刊》的一名驻外记者甚至有自己的主厨。
而现在,无论是读者还是广告商,都被吸引到了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上,在那里谁都可以发布信息和意见,谁也都可以获得这些东西。
尽管The Daily无需承担纸质版的印刷和发行成本,但它在技术上的投入巨大,包括从一开始就探寻用户究竟会如何使用导航;或是给图片加上特效,使得人们在划过这些图片的时候能像“旋转木马”一样旋转起来;又或是加入了语音评论功能;还有动态的,能让人们追踪自己所喜欢球队的新闻、图片、比分和Tweets的体育栏目。
还有一些新奇玩意,就像Google拥有无人驾驶汽车一样,它拥有一个MicroDrone MD4-1000无人驾驶飞行器。《福布斯》曾报道其在2011年6月将它放了出去,然后让它在洪水之后带来了北达科他州的消息。
Crunch Fund的合伙人和TechCrunch的专栏作家MG Siegier说,“如果每个人都知道它一年要花2500万美元,那可能早就能预见到其最终的结果了。”按照其平板上一年39.99美元的订阅费,没有广告支撑,The Daily需要赢得68.6万愿意订阅全年的用户。在2011年,它获得了10万个付费用户,虽然这看起来是个很不错的成绩。
但失败来得比想象得更快。
“The Daily没有强有力的品牌,而且它所制作的那种新闻有太多竞争对手。”Phillips说,“我想The Daily给所有传统媒体上了一课,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出版物可是没那么大用户需求的。”
The Daily的内容涵盖了当天的热点、商业、娱乐、科技和体育新闻,每篇文章的篇幅都不会太长,符合人们阅读的节奏,但却也不足以把那些有太多选择的人吸引过来。
“我们做出了很多出色的报道”,The Daily的一位高级编辑私下对The Daily Beast抱怨,“但这并不是必读的。”他的抱怨还包括The Daily居然有一个让木偶主持人主持的栏目,幕后还需要编剧写作脚本。“这是在浪费钱,我们本来应该直击调查性报道的。”他说。
一切都回到了那个问题—似乎是一个被忽略的问题,他们还是在失去读者群,这个事实没有改变。
在重新找回读者这件事情上,最近几年,《新闻周刊》唯一一次表现出了态度是它试图向《经济学人》靠近。在确认自己作为一份周刊再也无法和网站去竞争爆炸性新闻后,这家媒体开始加大了杂志中编辑的观点,专栏作家和特约作者的评论—当然,Tina Brown的人脉在其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这种尝试收效甚微,Tina Brown可以让众多名人聚在一起,但她没办法让他们统一意见。各种评论观点缺乏一致性的混乱没有为杂志获得读者的信任。而《经济学人》的评论方式则是它不署作者的姓名,在选题会上探讨出一个观点后,这就成为它在这个选题中的立场—一个观点,并且是有价值的观点,这是《经济学人》的价值。
“《新闻周刊》没有明确的目标用户。《经济学人》定位在经济学人和商务人士,《时代周刊》定位在公众,《新闻周刊》在两者之间徘徊,以至于它没有得到足够忠实的用户。”eMusic的CEO Adam Klein告诉《第一财经周刊》,他经历了技术给唱片行业带来的变革。
根据MPA的数据,《新闻周刊》的读者年龄中值是49.2岁,而整个杂志业是44.8岁。
更糟糕的是,Brown不止一次地制作出夸张、激进的封面:在2012年的5月,其封面文章把奥巴马称为“第一个同性恋总统”;在8月一期关于世界美食的封面,它用了一张充满性暗示的图片。
这一曾在《名利场》和《纽约客》时代管用的方法却不再有效。互联网上的用户的确会因此逗留并点击,但这无助于让这些用户成为自己的忠实订阅者—他们在网上已习惯于那些为吸引眼球而生的标题和照片。负面作用看起来更大。一些读者感到被冒犯,以至于不再对《新闻周刊》感到信任。在同性恋群体和女性主义者先后被上述两个封面激怒后,被《新闻周刊》激怒的还有穆斯林,民主党派,以及对新闻伦理持有严格标准的从业者。
不断滑落的发行量和广告收入,以及巨大的成本—Brown在一次采访中抱怨说,这本杂志每年的印刷和发行成本是4200万美元,在聘请任何一个作者、编辑或是美编之前这些钱就花出去了—终于让《新闻周刊》消失在传统纸质杂志的世界里。
但它的茫然远远还未结束。
有了新的产品形态,有了新的载体,有了新的产品背后那些新的潜在用户群,似乎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默多克拿出了十足的勇气,他曾宣称The Daily将会成为新闻被讲述和被消费的新模式。
但这还是改变不了,在一种新形式下,这仍然是一个旧产品的事实。
Instapaper和The Magazine的创始人Marco Arment在2011年9月写道:“这对于我这个只在互联网上读新闻的读者而言真奇怪,为什么我只关心其中的新闻、社论、App评论这一小部分,但是却要为这打包在一起的一堆内容都付费……这是一个旧世界的模式。”
他可能也是为数不多在The Daily创刊的时候就提出质疑的人。虽然他不是纯粹意义上的一个新闻从业者。
尚不知道The Daily的死亡是否给了Tina Brown某些触动。在不久前接受New York Magazine采访时,她表露自己还是着迷于那种老式的杂志,有着好的内容,广告构成其中的一部分,让文章融在其中,成为充实主体的一部分。
在她说“你去看看机场有多少人在用智能设备,我们想大胆尝试”时你会怀疑她的热情。她很少用Twitter,觉得那“过于自恋”;完全不用Facebook,因为“不想和认识的每个人都保持联系”。
在Brown的计划里,新的Newsweek Global价格和印刷版差距不大,单期4.99美元。她和她的同事在解释这种定价策略时说,媒体一直被广告商驱动,为了获得更多的广告而压低杂志价格试图覆盖到更多人群。现在,她不想讨好广告商了,她要看看“新闻的真实价值是多少”。
这意味着Newsweek Global将会和The Daily一样,在没有多少广告支撑的情况下,用订阅收入来支撑运营。
“最严峻的在于从纸质版向电子版转化的过程。很多人死于这样的过程,因为你既要承担电子版的花销,还要承担纸质版的固定成本。”Anand说。
“这样一种订阅收费的商业模式只在这种情况下有效—有明确愿意付费的目标读者,或能够提供独家信息给公众。”Adam Klein说。
Marco Arment创立的The Magazine在The Daily宣布死亡不久前上线。它和Brown心目中的优雅杂志相去甚远,恐怕和默多克心目中的也不同:两周出版一次,每期不过五六篇文章,是极客们关心的内容,没有插图,没有视频或互动游戏,没有广告。在最初,全部员工就只有Arment一个人。
但就像不停在为The Daily和《新闻周刊》寻找出路的人们所要求的,The Magazine有着可控的成本,找到了自己的读者群,以每期1.99美元的价格向他们收费。Arment在其博客中说,他的那些收入足以让他考虑再对The Magazine增加一点投资,例如提高作者的稿费,雇佣个编辑,增加点文章,或者加入点插图。
这未必就是未来杂志的方向。就像2000年初谁也没有想到那么多个行业即将被颠覆。
只是对于这些小成本的创业者而言,即使失败也不会像The Daily和《新闻周刊》那样疼痛。他们可以迅速抛弃被证明错误的想法,改变方向,在几天内拿出新的原型;而后者的失败意味着几千万美元的损失和一大票人的失业。
《新闻周刊》在其辉煌的顶峰时,发行量曾达到400万。The Daily则被寄予了太多的希望,似乎是新世界的开拓者,全世界都在观望着纸媒界的未来。但是2012年的12月,它们都走到了最后一期。
Tina Brown在那次New York Magazine的采访中说,现在她回想自己会接手《新闻周刊》简直太疯狂了,“那里没有执行主编,没有主编,没有新闻编缉,没有驻华盛顿的编辑,特写编辑。我想说—那里真的一个人都没有。有一些不错的年轻作者,但没有任何的管理架构……在(当年)去到《纽约客》的时候,那里都是聪明人。”
现在,她找不到足够多的聪明人来做这些事了。那些最聪明的人不再感兴趣了。